
点击右上角![]() 微信好友
微信好友
 朋友圈
朋友圈

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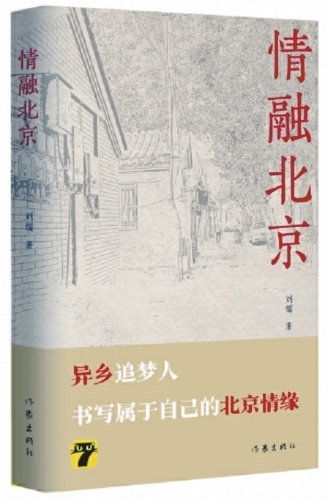
《情融北京》刘儒著/作家出版社 2024年6月版/68.00元
ISBN:9787521228649
○罗 岗
当我读着刘儒的长篇新作《情融北京》时,马上想到贾平凹在《秦腔》一书的后记中写道:“我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。”虽然《情融北京》和《秦腔》是很不一样的作品,但不无巧合的是,刘儒和贾平凹都是陕西人,贾平凹的家乡在陕南的商洛,而刘儒则出生在关中的凤翔。如果按照年纪来算,刘儒应该长贾平凹至少半辈,贾平凹是1971年进入西北大学中文系学习,刘儒则早在1963年就考取了北京政法学院。尽管他们的辈分有差别,不过都是农村的幸运儿,离开了农村,进入到城市,就像贾平凹说的那样:“我终于在偶尔的机遇中离开了故乡,那曾经在棣花街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,记得我背着被褥坐在去省城的汽车上,经过秦岭时停车小便,我说:‘我把农民皮剥了!’可后来,做起城里人了,我才发现,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,如乌鸡一样,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。”是的,他们“做起城里人了”,可“本性依旧是农民”。这种处于城乡之间夹缝中的位置,决定了他们的创作大体离不开“乡土文学”的范畴。
根据鲁迅先生当年对于“乡土文学”的经典理解,这种文学形态的关键在于:“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,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,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,从北京这方面说,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。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(G. Brandes)所说的‘侨民文学’,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,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,因此也只是隐现着乡愁,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扩读者的心胸,或者炫耀他的眼界。”(鲁迅: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二集·导言》)贾平凹的《秦腔》和刘儒的《情融北京》都处于“乡土文学”这一伟大文学传统的延长线上:之所以“隐现着乡愁”,是因为他们成了“城里人”;而“很难有异域情调”,则由于骨子里面“还是农民”。就像鲁迅评价蹇先艾的小说:“他所描写的范围是狭小的,几个平常人,一些琐屑事,但如《水葬》,却向我们展示了‘老远的贵州’的乡间习俗的冷酷,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——贵州很远,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。”
同样的,陕西也许离我们很远,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。贾平凹和刘儒曾经共同体会过农村改革开放带来的喜悦,“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的十年里,故乡的消息总是让我振奋,土地承包了,风调雨顺了,粮食够吃了,来人总是给我带新碾出的米,各种煮锅的豆子,甚至是半扇子猪肉,他们要评价公园里的花木比他们院子里的花木好看,要进戏园子,要我给他们写中堂对联,我还笑着说:棣花街人到底还高贵!那些年是乡亲们最快活的岁月,他们在重新分来的土地上精心侍弄,冬天的月夜下,常常还有人在地里忙活,田堰上放着旱烟匣子和收音机,收音机里声嘶力竭地吼秦腔”;也应该一起经历了“三农问题”给乡亲父老带来的阵痛,“可农村在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后,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城市,农村又怎么办呢?农民不仅仅只是吃饱肚子,水里的葫芦压下去了一次就会永远沉在水底吗?就在要进入新的世纪的那一年,我的父亲去世了。父亲的去世使贾氏家族在棣花街的显赫威势开始衰败,而棣花街似乎也度过了它短暂的欣欣向荣岁月。这里没有矿藏,没有工业,有限的土地在极度地发挥了它的潜力后,粮食产量不再提高,而化肥、农药、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税费迅速上涨,农村又成了一切社会压力的泄洪池。体制对治理发生了松弛,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,像泼出去的水,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,来了也抓不住,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,农民是一群鸡,羽毛翻皱,脚步趔趄,无所适从,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,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”。
假如说在《秦腔》中,贾平凹还看不太清楚这些“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”的农民的命运如何,他只是朴素地认识到,“对于农村、农民和土地,我们从小接受教育,也从生存体验中,形成了固有的概念,即我们是农业国家,土地供养了我们一切,农民善良和勤劳。但是,长期以来,农村却是最落后的地方,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。当国家实行起改革,社会发生转型,首先从农村开始,它的伟大功绩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,虽然我们都知道像中国这样的变化没有前史可鉴,一切都充满了生气,一切又都混乱着,人搅着事,事搅着人,只能扑扑腾腾往前拥着走”;那么20年过去了,伴随着时代的发展,刘儒在《情融北京》中,不仅体会到了“农民离开土地”之后的虎虎“生气”,而且正在展望他们“扑扑腾腾往前拥着走”的美好前景。在其笔下,孙玉爱、成跃山等三家六个人离开陕西农村,来到北京打工,虽然也不乏艰辛,甚至遭遇了不小的危机,但他们用农民特有的朴素、善良、隐忍和坚持,克服并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,在城市中逐渐站稳了脚跟。就像小说题目《情融北京》所彰显的,这群“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”的农民,不只是进入了城市,而且融入了城市。他们不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,而且因为他们的进入和融入,也重新规划、改变甚至创造了城里人的命运。
在这个意义上,刘儒作为“乡土文学”传统的当代传人,其小说不单是“献给故乡”的“薄礼”,同时,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理想见证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