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点击右上角![]() 微信好友
微信好友
 朋友圈
朋友圈

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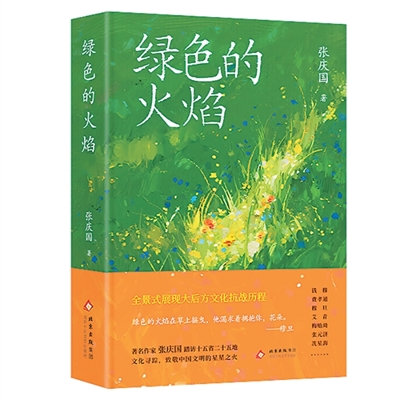
“国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”,“草木深”本指荒草凄凄,我也可以理解为文明之火的摇曳,但穆旦的诗《春》中的两句更合适:
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,
他渴求着拥抱你,花朵。
战争之恶面前,文明的花坚持开放,给人类送去了生活的勇气与信心。我的新书《绿色的火焰》(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)写抗战后方的文化活动,难度很大,我反复思索:战争时期保命要紧,还有什么更要紧?抗日战争的炮火中,中国文化毁灭停滞了,还是在继续存续甚至发展?人类在战争年代除了活着还能做什么事?我眼前亮了,有了写作的方向。
这是一部多方位描述中国文化人活动的文学作品。写一个文人没问题,写各行业的一批文人难度就大。出现困难我就来劲,我喜欢做有挑战的事。我接着向自己发出追问:这段历史中有多少人该写?我要学习哪些行业的专业知识?我需要采访吗?找谁采访?我面对的事件已成为历史,找不到健在的当事人采访,找到当事人的后代,他们也都年事已高,他们的讲述是历史事实,还是私人感情?
相比古代史,抗战史更近,资料也繁杂,怎么选择?经人介绍,我结识了一位杰出的抗战史学者,在他的指导下,我用半年时间全面学习抗战史和抗战文化史,也学习了中国现代音乐史、戏剧史,世界出版史、文物知识等,我又购买了30多本人物传记,研究抗战时期中国人的生活与行为方式,也研究一些文化名人的性格和家族史,包括一些地方史和地方风物志。那半年我读得日夜颠倒,高度兴奋,理出一个写作提纲,确定了写作内容。
还有疑问,一部纪念抗日战争的非虚构作品要怎么写?单纯重现往事吗?历史著述早有史学家写过了,史料也有专家做过整理记录,作家的文学表达空间在哪里?很多历史现场已经改变或不复存在,我出行调查的意义是什么?我思考再三,一时理不清头绪,只明白一点,历史不能坐在家中写,要去现场观察,先上路再说。
我首先寻访七七事变起始地北京卢沟桥与宛平城,接着去天津南开大学。我在天津的老街寻找张伯苓故居,曾遭遇居民的阻拦,这没事,我理解,不容易就更有内容可写。我再去上海和江苏南京等地,用3个月时间,走遍中国15省份25地。我都坐火车,保持跟大地的接触,都挑靠窗的座位,一直在车上注视窗外山河的移动,捕捉窗外一晃而去的房屋和路边的人脸。
我一边在中国大地上行走观察和体验,一边躺在陌生城市酒店的床上,面对头顶的黑暗,紧张思考,做出并推翻各种写作规划。随着行走路线的延伸,我的思维渐渐清晰。我明白了两点:第一,我要用人物来架构这部书,这应该是一部描述人物生命史的作品,我不能写那种见事不见人的文字;第二,我认为外出调查很重要,必须到达所有将写到的现场,但我不应该止于调查,我行走的另一个重要意义,是积累今人寻找时间的体验,我的写作,是一段时间跟另一段时间的相互注目。
我有事做了,我把出行做田野调查的行程、坐的车、吃的饭、住的旅馆、见到的人和如何见到这个人,以及调查途中我的感情和思想活动记下来。在南京长江边的浦口火车站,我坐在路边的椅子上,用手机写了一小时,记录下现场的建筑、行道树、商店、江水、轮船的汽笛声、路人的姿势表情以及我的思想和情感活动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的街头,我找不到椅子,坐在街边的石墩上,也在手机上写了半小时。在广西河池寻访浙江大学西迁遗址的荒园,我请带路的朋友在车里等,自己站在荒园门口的阳光下,现场记下几百字。我每天晚上回到酒店,赶紧打开电脑,写采访日记,把手机上的文字取出来,再写下当天所见。搜索现场的心情,回味和思索当天行动中的思想震荡,经常持续到半夜。纵贯整个中国的寻访调查结束,我写下了15万字的采访日记。
于是,我后来写作的文本中,出现了两条叙述的河流,一条是历史事件,宽阔的记忆之河,一条是纤细的现实之水——穿越中国行走的“我”。我用文学的方式来描述记忆之河,也用细致的文学描述写下现在“我”之所见所思,“我”与历史隔着时间大河对望,拓宽了文学艺术的时空。
这是一个文学形式的问题,单纯地重述历史是一种平面写作,写历史的同时,再写今天的“我”,层次会丰富。“我”在中国行走万里寻访历史现场的经历,也是书中的重要内容,“我”的视角和目光,“我”的行动,在全书的文本中与抗战时期张元济、梁思成、穆旦、冼星海等文化人的活动相互注视,整部书的叙述就呈现出立体效果,变成复调式表达,这种写法应该更好。
我这部作品的主题是向人类文明致敬,我的文字是向颠沛流离的战争年代继续文化工作、并为中国作出杰出贡献的文人表达遥远问候,是为了探究他们社会情怀的宽度、深度以及文化与人类社会进步的关系。文化是一个复杂的人类生活内容,一方面它传授知识,教人研习前辈的智慧,创造更好的生活;另一方面,它还塑造强大的人格,给人注入超越物质生存需求的精神力量,教人目光远大,具有社会责任感,无私、善良和高尚。
中国有崇文重教的传统,文人治国的历史很长,孔子供在庙里接受人们顶礼膜拜,城里有文庙,乡下的魁星阁还供个持笔的神仙,读书受到高度重视。立德立功立言,是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“三不朽”。现代社会文化多元,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独立于精神修炼之外的文化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调动最好的艺术手段,追溯抗战时期中国文人舍生忘死工作、并坚持为社会服务的历史切片,对后人会有启发和激励,把这些写出来,也算我一份微薄的文化贡献。
作者:张庆国
